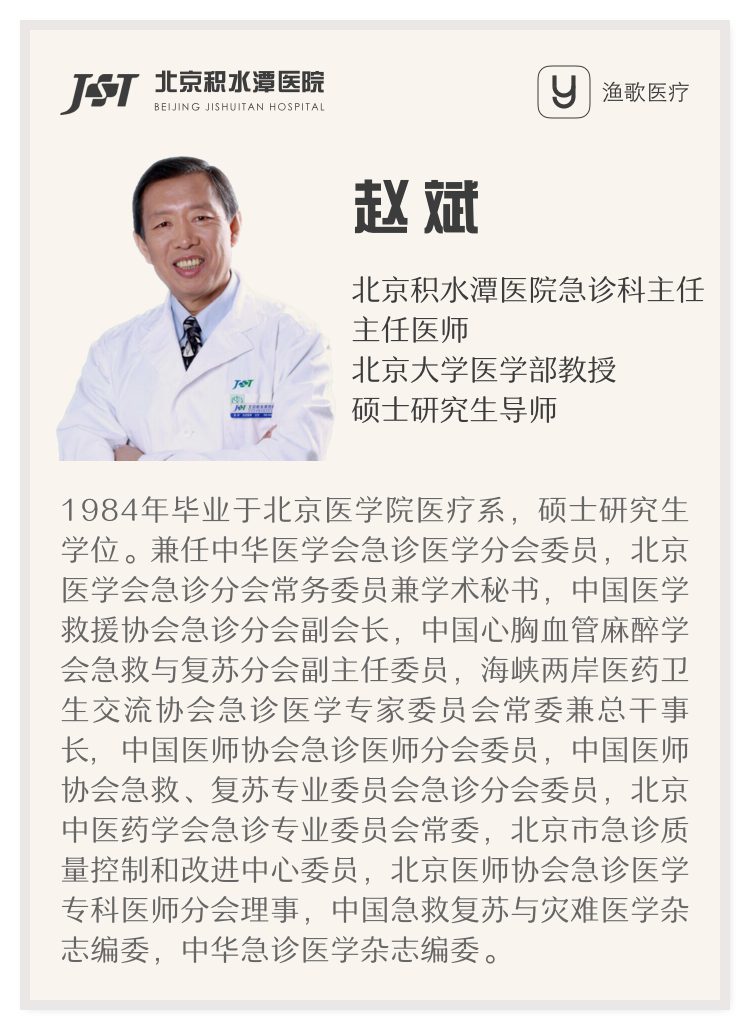读了西格里格斯写的《西医文化史——人与医学》,有了想写病人是谁的冲动。作为医生当然应该知道谁是病人,那就是有疾病缠身的人就是病人。可认知到这一步对医生来讲就可以了吗?如果从疾病层面确定病人,应该是足够了。可要是从人的层面看待疾病就显得不全面了。换句话说,从生物医学模式看病人,就是看疾病,从生物-心理-社会医学模式看病人,就要从三个角度看疾病的属性,也就是人的属性。所以,社会赋予了病人一种独特的地位。“医生的难题不只是在解剖意义上使病人恢复健康,那仅仅是治疗他,直到他所有的器官从结构上、功能上跟他生病之前的状态一个样。完全康复,尽管非常诱人,却非医生责任的全部。要等到他使得那病人摆脱孤立的社会地位,使其失而复得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的身份。同时,一个伤疤、一种畸形、身体附件的缺失,病愈之后的种种迹象,只要这一切不会永久性地影响一个人工作和获取乐趣的能力,这时医生的难题才算彻底地解决。”

Photo by Arvin Chingcuangco on Unsplash
现在许多医生,包括我在内,并没有深刻认识到病人的社会属性,非病人之外的人也没有感受到疾病给病人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,包括孤独、恐惧、耻辱、被边缘化的感觉。当然这些疾病观的形成都是有历史渊源的,在原始社会没有证据显示人类掌握了治疗技艺的任何知识,人有了小病小灾,包括磕磕碰碰的外伤,不被认为是疾病,继续和部落里的人一样地生活。但如遇到被类似天花这样强烈的传染病侵袭的人,就不得再参与部落的生活,疾病使人孤立。在苏门答腊有一个叫库布人的种族,他们从来不问致病的原因,谁得病,谁就自动从他习惯了的处境当中退出。以后发展到了更高程度的文明阶段,人们新的观念是,病人不是无辜的牺牲者,而是深受苦难去赎他的罪,病是罪的惩罚。但不管怎么样,在远古社会病人与健康人之间,存在着巨大的落差,得病实际就等于死亡。
病人地位最深刻、最具决定性的变化,是由基督教带来的。与那些只适合于健康之人的古代宗教相比,基督教应许了对心灵和肉体的疗救。疾病不再被认为是因某人自己或他人的罪孽而得的污点和惩罚,疾病也没有使人低人一等。怜悯成了社会的精神特质。4世纪初许多医院建立了起来,这些医院不是出于种种有利可图的考虑而建的。6世纪以后,看护病人的责任大多由修道院来承担,修道院的院长要求僧侣们铭记护理病人的重要性:治愈之先,护理僧要给病人以爱。由此看来,随着社会的发展、科学的进步、宗教文化素养的提高,对疾病的认知、对什么是病人的理解,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在这里,较比过去病人是最大的受益者。
但也不能不承认,那些古老的疾病观,不管对现在病人的心理,还是在今天医生的眼里,都遗留下了不少后遗效应。“我们都知道,生病之人是一个落难之人,病对他而言就是命运的安排,就意味着经受痛苦。病人对疾病的态度与对别的苦难并无二致,这态度只在各各不同的人之间有所区别;这取决于他的年龄、性别、种族以及受教育的程度。而且根据这个病人的气质和性格,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起伏;显然,病的严重性以及病的种类也起了作用。”可往往医生们还是喜欢用一成不变的思维看待眼前每一位病人,医生的兴趣在治病,缺少考虑病人各自独特的感受。

Photo by Toa Heftiba on Unsplash
“人”不能单用解剖学和生理学去理解,如果是修理一台有缺陷的机器,也许这样就够了。但是病人首先是并且最重要的是一个陷在痛苦之中的人。得病使人变得自我,使人愈加敏感,除了躯体病以外,病人从里到外再也不是得病前的那个健康人。他是一个精神受到折磨的人,一个不得不面对强烈沮丧的人,一个其生命机能面临崩溃的人。所以,当每位医生看到病人的时候能否抽身于疾病之外,想到病人的强烈自我意识,实际就是要求医生把每个病人都当成一个有思想、有情感的人来对待。
病人是谁?当然还是那个得病的人,只是他的痛苦不仅仅是病,还有与社会隔离后的孤独和被遗弃感,有疾病给他带来的无形压力和恐惧,有渴望求得所有人都关注的被爱心理。病人是整体,有生命力,有头脑。疾病是部分,不会表述,没有知觉。所以,医生看病应该看的是病人,不是单一的疾病。在医生的脑子里对病人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轮廓,人受到了疾病的侵扰,出现了痛苦,有躯体痛和心理痛。医生解决躯体痛刻不容缓,同时治疗心理痛也不要拖拖拉拉。
西格里格斯说:“对医生来讲,单单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观察,是不够的。医生要仔细考虑人在自然界里孤立的地位,也要认识到人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生命。他必须和人的整体打交道,必须对待生命体验的总和。”